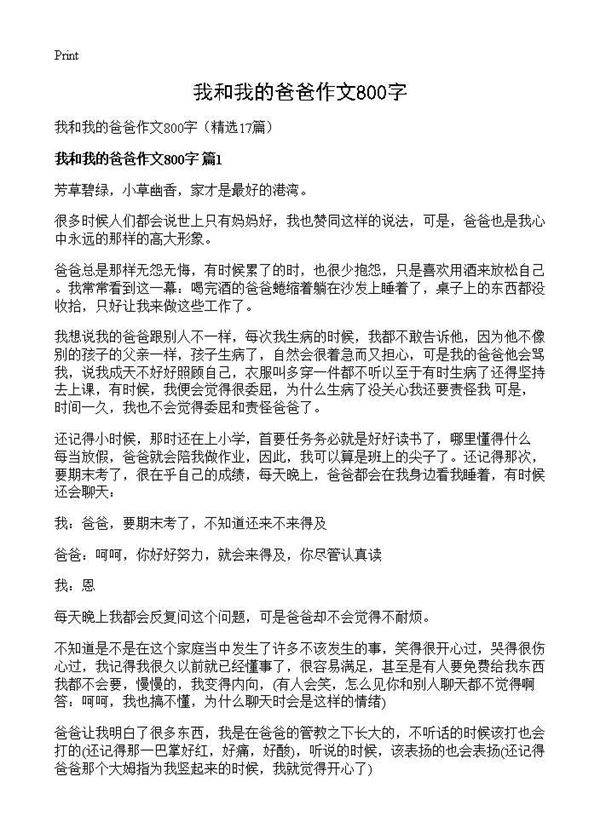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,窗外飘着鹅毛大雪。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,额头滚烫得像块火炭。爸爸用粗糙的大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,二话不说就背起我往医院跑。他的棉袄被雪水浸透了,却把我裹得严严实实。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,能听见他急促的喘息声和踩在雪地上"咯吱咯吱"的脚步声。路灯的光晕里,我看见爸爸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凝结,又消散在夜色里。那一刻,我突然发现爸爸的后背已经不像记忆中那样挺拔了,他的鬓角不知何时也悄悄爬上了银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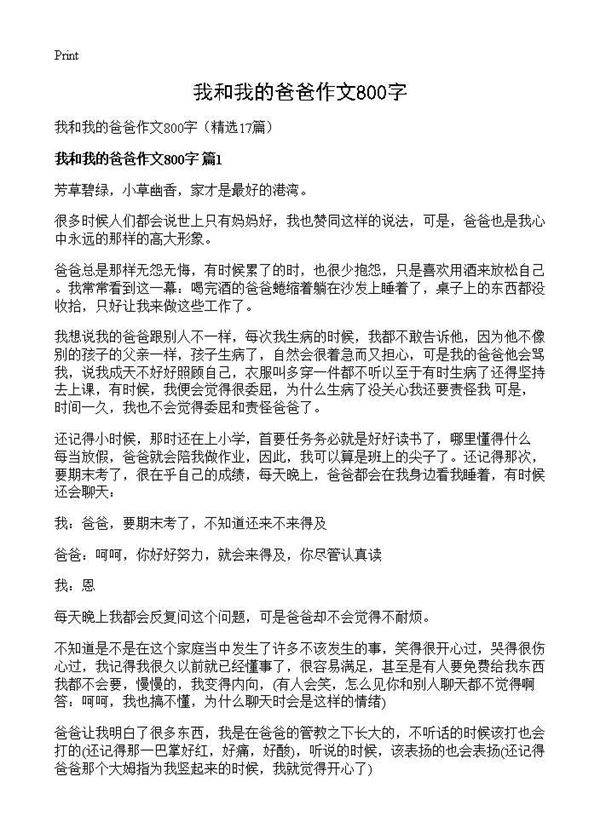
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,窗外飘着鹅毛大雪。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,额头滚烫得像块火炭。爸爸用粗糙的大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,二话不说就背起我往医院跑。他的棉袄被雪水浸透了,却把我裹得严严实实。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,能听见他急促的喘息声和踩在雪地上"咯吱咯吱"的脚步声。路灯的光晕里,我看见爸爸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凝结,又消散在夜色里。那一刻,我突然发现爸爸的后背已经不像记忆中那样挺拔了,他的鬓角不知何时也悄悄爬上了银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