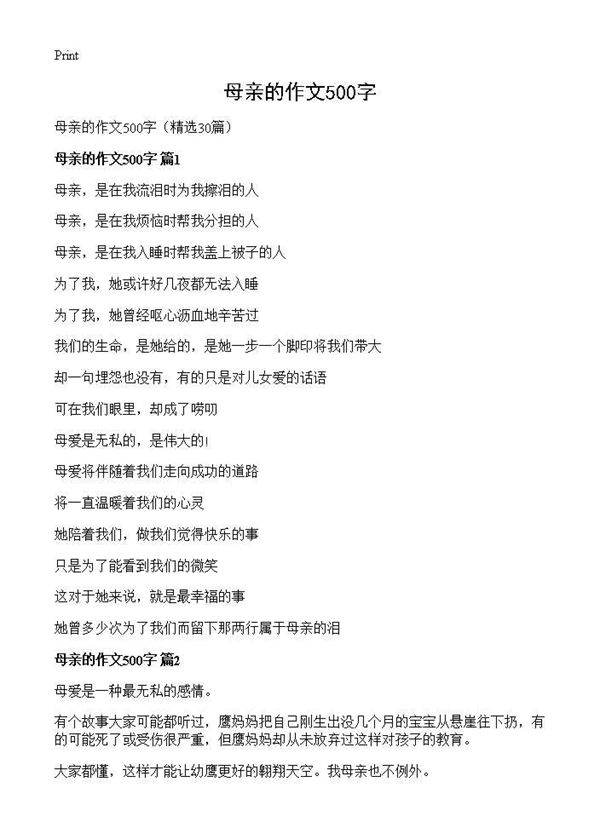记得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,我突然发起了高烧。迷迷糊糊中,看见母亲披着单薄的外套在药箱里翻找体温计。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拨开我被汗水黏在额前的碎发,把体温计小心地放进我腋下。当看到水银柱停在39度时,她倒吸一口气,立即用温水浸湿毛巾为我擦拭身体。我半梦半醒间,总能感觉到她每隔半小时就来换一次冰毛巾,那双手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得通红却始终温暖着我的额头。天蒙蒙亮时,烧终于退了,而母亲眼下的青黑告诉我,她又为我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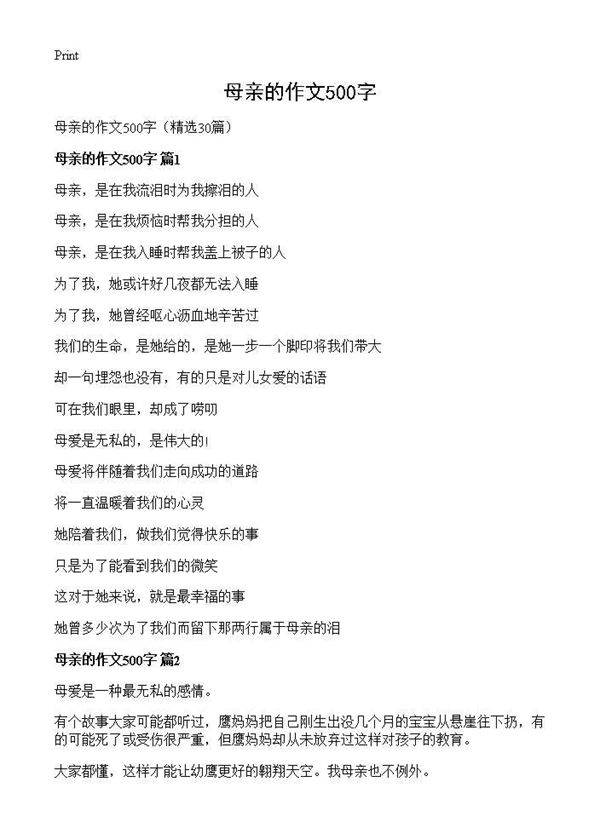
记得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,我突然发起了高烧。迷迷糊糊中,看见母亲披着单薄的外套在药箱里翻找体温计。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拨开我被汗水黏在额前的碎发,把体温计小心地放进我腋下。当看到水银柱停在39度时,她倒吸一口气,立即用温水浸湿毛巾为我擦拭身体。我半梦半醒间,总能感觉到她每隔半小时就来换一次冰毛巾,那双手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得通红却始终温暖着我的额头。天蒙蒙亮时,烧终于退了,而母亲眼下的青黑告诉我,她又为我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