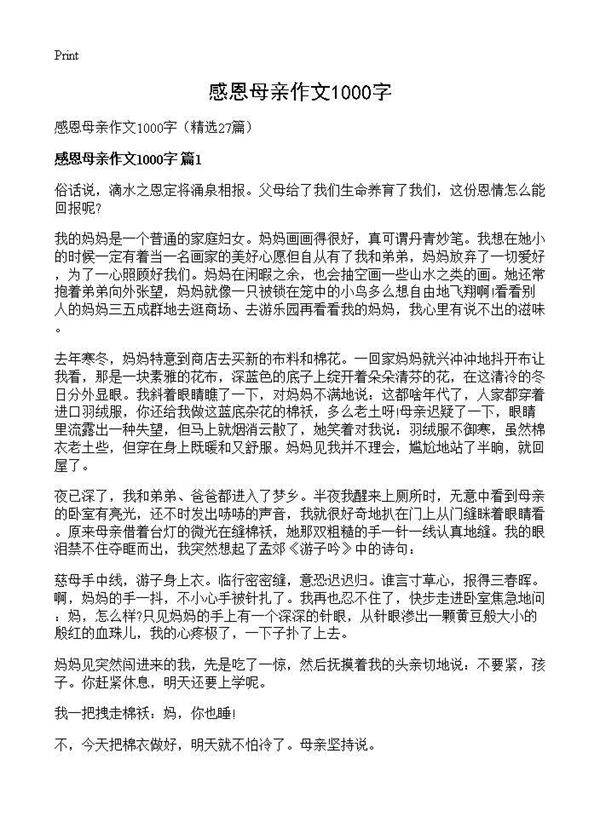母亲的爱如同春天的细雨,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的心田。记得去年冬天我发高烧,母亲整夜未眠,用冰毛巾一遍遍为我擦拭滚烫的额头。她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时,我闻到她指尖残留的葱花香——那是她刚放下为我熬粥的锅铲就赶来照顾我的证明。凌晨三点,我迷迷糊糊看见她跪在床头,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数退烧药的颗粒,花白的鬓角在灯光下泛着温柔的银辉。药很苦,但她总会变魔术般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,剥开糖纸的声音像夜风里清脆的风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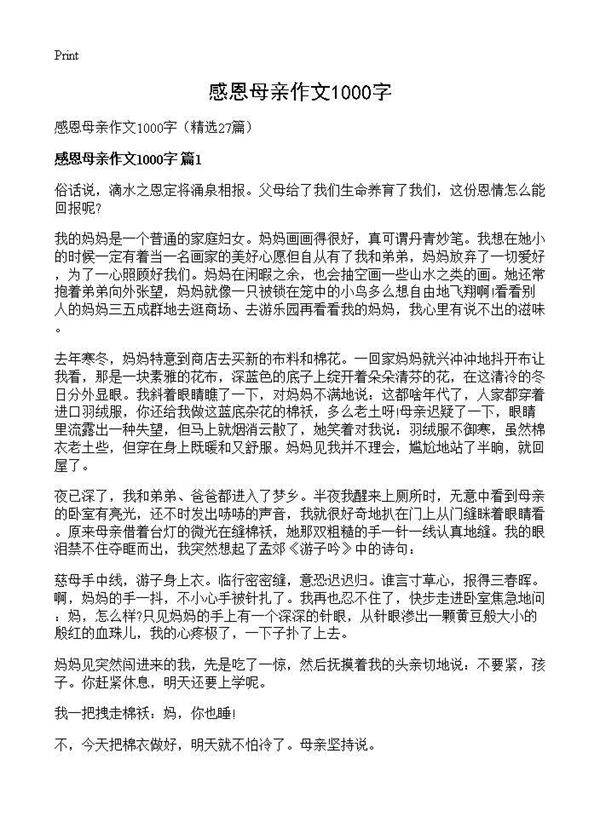
母亲的爱如同春天的细雨,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的心田。记得去年冬天我发高烧,母亲整夜未眠,用冰毛巾一遍遍为我擦拭滚烫的额头。她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时,我闻到她指尖残留的葱花香——那是她刚放下为我熬粥的锅铲就赶来照顾我的证明。凌晨三点,我迷迷糊糊看见她跪在床头,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数退烧药的颗粒,花白的鬓角在灯光下泛着温柔的银辉。药很苦,但她总会变魔术般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,剥开糖纸的声音像夜风里清脆的风铃。